思想纵横|胡爱玲: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工具理性评析
□胡爱玲
西方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后,产生了诸多变化。包括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效率的提高及量化指标的普遍推行等等。相较于农业文明社会,工业文明社会中的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必须将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等活动合理化,以保证资本积累和扩张持续。否则,很容易被市场淘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政府及其他管理部门纷纷采用工具理性思维模式推进生产和生活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努力从众多特殊性的事件或事实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则、规范等,并以此为确定的标准来要求被考核对象遵从。客观上,它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成本,量化下的评定也显示出公平和公正的一面。可是随着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合理化运动深入进行,社会发展越发显示出背离价值理性的负面效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文化困境,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深受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以上情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进行剖析,并指出改变的具体思路,比如卢卡奇、列斐伏尔、哈贝马斯等。他们认识到工具理性倡导过渡,价值理性缺失会让人陷入困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应并行不悖,但整体社会对“精于算计、效率至上”的推崇,引发了生存意义危机。价值理性强调行为人的动机高尚,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等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主旨。正是因为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使很多无法被量化的也量化起来,包括人的心理状态。它在激发人积极向上、珍惜时间、渴望功绩的同时,也打乱了人生产、生活的节奏。卢卡奇批判说受工具理性支配的人,是客体化、数字化和原子化的人,他们缺少爱与关怀,被严重物化,不会也不愿做出改变。列斐伏尔认为人的身体和生活节奏被社会节奏裹挟,节奏紊乱给人种种不适感,他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的人。哈贝马斯用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来总结这一社会现象,强调本应充满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却遵循着行政管理和市场交易的规则。人开始拒绝崇高,视他者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或纯粹的客体。这严重影响了人与自身、社会之间的关系,人无法建立起自我和社会的统一性。
鉴于上述情况,他们分别提出自己的解决问题思路。卢卡奇认为物化程度最深的是无产阶级,他们长期被精细分工限制,不能从总体上了解和认知社会的运行机制,对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不了自觉的认识。必须有先进的组织来领导他们开展各项工作,充分调动他们改变现实、创造自我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列斐伏尔分析指明,总体性的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人内在地具有改变现实、超越现实的冲动,应该从批判日常生活开始,反思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人应遵从自身的节奏和自然的节奏,无需在忙碌中迷失自我,更不应该将程式化的生活视为常态,反而应该从节日庆典中看到人最为真实的需求和动力。哈贝马斯倡导社会成员要加强学习和道德实践,熟知理想的言语情景,培养和提升自己的交往资质,用交往理性补充工具理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容忍,在差异中寻求共识。
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合理化运动得到了规约,但是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快节奏生活带来的精神困惑,包括《加速社会》、《倦怠社会》中提及的一些类似社会现象时有发生。我们亟待反思西方工业文明推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正确看待工具理性中“效率至上、规范化、标准化和量化考核”对主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从生理、心理、兴趣、认知及接受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统一的思维模式、同一的量化标准恰恰抹杀了个体的差异;程式化的管理评价标准虽然力求做到客观,但不是绝对的正确。这就决定了片面地按照工具理性思维模式考察主体及其能力是有损于主体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样态都不能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观点。人的思维直接影响人的行为,当人不被当作自主思考的主体时,他们会丧失超越现实的理想维度,失去生活动力。个体只有拥有能自主判断的交往资质,才能积极地制定、反思和质疑规则,抵制日常生活中工具理性过度挤兑价值理性导致的意义和价值虚无感。保证个体以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为交往媒介主动融入共同体,为推动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本文为郑州大学教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究式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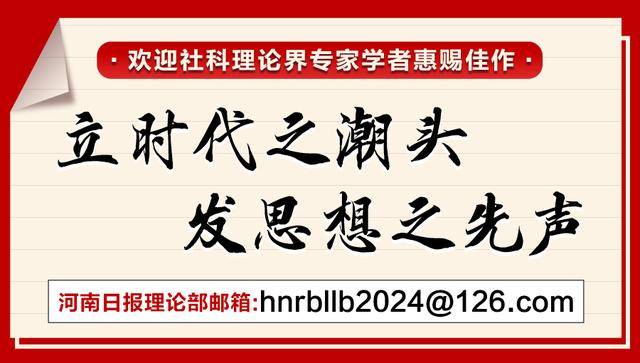





评论